我是被村庄里的开门声唤醒的。这座沉睡的村庄,可能只有一个早晨,剩下的全是被别人过掉的夜晚和黄昏。有的人被鸡叫醒,有的人被狗叫醒。醒来的方式不一样,*活和命运也不一样。被马叫醒的人,在远路上,跑顺风买卖,多少年不知道回来。被驴叫醒的人注定是闲锤子,一辈子没有正经事。而被鸡叫醒的人,起早贪黑,忙死忙活,过着自己不知道的日子。虚土庄的多数人被鸡叫醒,鸡一般叫两遍,就不管了。剩下没醒的人就由狗呀、驴呀、猪呀去叫。苍蝇蚊子也叫醒人,人在梦中的喊声也能叫醒自己。被狗叫醒的人都是狗命,这种人对周围动静天*担心,狗一叫就惊醒。醒来就警觉的张望,侧耳细听。村庄光有狗不行,得有几个狗一叫就惊醒的人,白天狗一叫就跑过去看个究竟的人。
一个早晨大家都醒了。什么都没有耽误,因为瞌睡睡足了,剩下的全是清醒。人们没日没夜的干,那点开荒的活在落雪前也就干完了。整个冬天人没有瞌睡,沿着野兔的路,野羊和野骆驼的路,把远远近近的地方走了一遍。后来这些路变成人的路,把虚土庄跟远远近近的村庄连在一起。
她最后的盛开没有人看见。那个夜晚,风声把每个角落喊遍,没有一粒土吹动,一片叶子飘起。她的儿女子孙,睡在隔壁的房间里,黑暗中的呼吸起起伏伏。一家之长的大儿子,像在白天说话一样,大声爷气的鼾声响彻屋子。妻子在他身旁轻软地应着声。几个儿女长短不一的鼻息表现着反抗与顺从。狗在院墙的阴影里躺着。远远的一声狗吠像是梦呓。院门紧闭。她最后的盛开无声无息。没有人看见那朵花的颜色。或许她是素淡的,像洒满院落的月光。或许一片鲜红,像心中看不见的血一样。在儿孙们绵延不断的呼吸中,她的嘴大张了一下,又大张了一下。
多少年后他们听见她的喊声,先是儿子儿媳,接着孙子孙女,一个个从尘土中抬起头,顺着那个声音,走向月光下洁白的回返之途。在那里,所有道路被风声扫净。所有坎坷被月光铺平。
弟弟脸朝西侧睡着,我也脸朝西,每晚一样,他先睡着,我跟在后面,迷迷糊糊走进一个梦。听刘二爷说,梦是往后走,在梦中年龄小的人在前面。
你被马车拉到这一家的那个早晨,我就坐在房顶。老头说。我看见他们把你抱到屋里。你是唯一一个睡着来到村庄的人。我不知道你带来一个多么大的梦,你的脑子里装满另一个村庄的事。你把在我们村里醒来的那个早晨当成了梦。你在这个家里的*活,就这样开始了。你一直把我们当成你的一个梦,你以为是你梦见了我们。因为你一直这样认为,我们一村庄人的*活,从你被抱来睁开眼睛的那一刻,就变虚了。尽管我们依旧像以前一样实实在在的*活,可是,在你的眼睛中我们只是一场梦。我们无法不在乎你的看法。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活在怎样的*活中。我们给了你一千个早晨,让你从这个村庄醒来。让你把弄反的醒和睡调整过来。一开始我们都认为这家人抱回来一个傻子,梦和醒不分。可是,多少年来,一个又一个早晨,你一再的把我们的*活当成梦时,我们心里也虚了。难道我们的*活只是别人的一个遥远睡梦。我们活在自己不知道的一个梦里。现在,这个梦见我们的人就走在村里。
从那时起,我们就把你当神一样看,你在村里做什么都没人管。谁见了你都不大声说话。我们是你梦见的一村庄人。你醒了我们也就不见了。烟一样散掉了。不知道你的梦会有多长。我们提心吊胆。以前我看远处路上的尘土,看进出村子的人。现在我每天盯着你看。我把梯子搭在后墙,让你天天看见梯子。有一天你会朝上走到房顶。我等了你好多年,你终于上来了。我得把前前后后的事给你说清楚,你肯定会认为我说的全是梦话。你朝下看一看,你会不会害怕,眼前的这个梦是不是太真了。
每个夜晚都有一个醒着的人守着村子。他眼睁睁看着人一个个走光,房子空了,路空了,田里的庄稼空了。人们走到各自的遥远处,仿佛义无返顾,又把一切留在村里。
醒着的人,看见一场一场的梦把人带向远处,他自己坐在房顶,背靠一截渐渐变凉的黑烟囱。每个路口都被月光照亮,每棵树上的叶子都泛着荧荧青光。那样的夜晚,那样的年月,我从老奇台回来。
我想把他抱到沙枣树下,把我睡觉的那片炕腾出来,我已经瞌睡得不行了,又担心他的梦回来找不到他,把我当成他的身体,那样我就有两场梦。而被我抱到沙枣树下的那个人,因为梦一直没回来,便一直不能醒来,一夜一夜的睡下去,我带着他的梦醒来睡着,我将被两场不一样的梦拖累死。
梦是认地方的。在车上睡着的人,梦会记住车和路。睡梦中被人抱走的孩子,多少年后自己找回来,他不记得父母家人,不记得自己的姓,但他认得自己的梦,那些梦一直在他当年睡着的地方,等着他。
夜里丢了孩子的人,把孩子睡觉的地方原样保留着,枕头不动,被褥不动,炕头的鞋不动,多少多少年后,一个人经过村庄,一眼认出星星一样悬在房顶的梦,他会停住,已经不认识院子,不认识房门,不认识那张炕,但他会直端端走进去,睡在那个枕头上。
从那时起,我知道村庄的夜晚*长另一些粮食,它们单独*长,养活夜晚醒来的人。守夜人的粮食也长在夜里,被月光普照,在星光中吸收水份营养。他们不再要村里供养,村里也养不起他们。除了繁衍成大户人家的守夜人,还有多少人*活在夜晚,没人知道。夜里我们的路空闲,麦场空闲,农具和车空闲。有人用我们闲置的铁锨,在黑暗中挖地。穿我们脱在炕头的鞋,在无人的路上,来回走,留下我们的脚印。拿我们的镰刀割麦子,一车车麦子拉到空闲的场上,铺开,碾扎,扬场,麦粒落地的声音碎碎的拌在风声里,听不见。
天亮后麦场干干净净,麦子不见,麦草不见,飘远的麦以不见。只有农具加倍的开始磨损。
那个晚上,我好像就睡在村里。哪都没去。我只是看见我从远处回来,被一渠水挡住。我安安静静,没有喊一声,也没起身,提一盏灯走出去。我的记忆在那一刻中断了。以后我去了哪里,回到哪个村庄,我记不清了。我老了以后,时常靠在墙根,晒着太阳,想不清曾经的哪一种*活,使我变成现在的样子。我的腿是在梦中跑老的还是现实的一件小事把腿跑坏了。我真正的*活我从来没有看见过。
她醒来时我正在做梦,她喊我,摇我的肩膀和头。我隐约听见她的喊声,急急的往回赶,多少年的路啊,眼看就到了,看见房子、院门和窗户,看见门里的人影。突然的,大渠上的桥断了,水黑黑的往远处流。多少年前一个夜晚,我被它挡住,好像挡住的不是我,我那时正睡在村里,应该40岁了,我在等我的孩子回来,我睡一阵醒一阵,想不清自己有几个孩子,好像总有一个没回来,我听见他的脚步声,在路上,在村巷里走,他没有玩够,还是记不起家了。我出去寻找时村里村外的路上只有月光,墙头树梢也是月光。星星静静的。我不敢喊,我回去睡下时,那个脚步声移到村外的荒野,步子小小的,像一个五岁孩子的脚步。
我在荒野上拾了一个女人,她睡在青草中,看样子睡了很久了。我没想惊醒她。到处是睡着的人,路上,房顶,草垛,还有庄稼地里。到处是人的梦,粘粘糊糊。我撇开路,向荒野中走,我想离开村子,到稍远些的星光下透透气,依旧没走过去。我被睡在青草中的一个女人挡住。
原来我踏上的荒野也是一条路,我在草根下看见以前的车辙和马蹄印。这个女孩可能在路上走着走着睡着了。她那个年龄,梦多得晚上根本做不完,白天走着也在梦,吃饭喝水也在做梦。她睡着后这条路荒掉了,因为一个人睡在路中间,所有脚步远远绕开,所有车马绕开,以后的秋收春播移向别处,路旁的地大片长荒。再没人走过这里。因为一个女孩子的梦和睡眠,这片荒野上的草木,开紫花,结紫果。
有几年,我在虚土庄周围,绕着它一圈一圈的转。我不能把一个睡着的女人带回家。我得把她弄醒。
我那时多自在呀,整天背着手在村子里转悠,走到谁家不想走了,就住下来。有好吃好喝好睡。他们在转世界,我在转一个村庄。从村南头走到北头,就是一年光景。遇到我喜爱的女人,我会多住些日子。村长嘛,按村里人说法,就是闲锤子。庄稼在地里长,村长在被窝里忙。
许多人一次次的走进别人家,倒头睡着,过着自己不知道的另一种*活。跑远路的人带回无穷的瞌睡。好像他们在外乡从未闭过眼睛。他们回来只是找一个炕,倒头大睡,所有白天被睡完,醒来依然是黑夜,到处是睡着的人,路上、院子、草垛房顶,横七竖八睡着人。睡在路上的人最多,因为许多人走着走着,一歪身倒在路上睡着。夜行的马车,看见路上睡着人,远远绕开。如果有许多马车绕开,天亮后地上就出现一条新路。睡着人的那段路一夜间荒草丛*。每次醒来,谁都不敢保证自己只睡了一夜,这一觉醒来,是多少个白天黑夜之后,谁知道呢。梦中天亮过无数次又黑了。睡眠是多么地久天长的事情。总有人从别人家炕上醒来,揉揉眼睛又上路了。他找不到一个醒着的人,问:我怎么回不到自己家,一觉醒来总是在别人家炕上。
而在一片荒草、几棵树、半截篱笆墙外的自己家里,昏睡着一个陌*人。满院子是他的梦。屋顶上空是他如雷的鼾睡。
我在等刘榆木醒来,说个事情。他靠在麦草堆上扯呼,说梦话。我不知道他还要睡多久。太阳移到麦草堆后面去了。谁家的麦场,麦子早打完拉入仓了,丢下一堆麦草,一群麻雀在四周飞叫。我闲逛过来,见睡着的刘榆木,突然想起,去年秋后,压冬麦的时候,刘榆木借了我们家一根麻绳,一直没还。可能都用成麻丝了。我得问问他,把麻绳要回来。
现在,我要等一个人醒来,说件正经事。一根绳子的事。我希望鸟吵醒他。鸟不敢飞近。我不能吵醒他。我坏了他的梦,他会把我当仇人。我们这个地方的人,太爱惜别人的梦,醒来你怎么整他,欺负他都行,一个人做梦的时候,千万要尊重,不能惊动别人的梦。白天你勾引人家的媳妇都行,晚上不能扰了人家的梦。让人自己醒来。不能自己醒来的人最好睡在村子里,即使独家住在荒野上,也要养至少五种牲畜。鸡叫不醒人,牛会接着叫。牛叫不醒,还有驴和马。要由着人的睡梦,一觉睡到老的人,我不是没有见过。
等着等着我睡着了。我睡着时,被谁唤去割了大半天麦子。
这么多年,我在梦中干的活,做的事,比在白天多得多。尤其在梦中走的路,比醒来走的更远。我的腿都在梦中跑坏了,可我还呆在村里。
我很小,还不懂怎么*活时,母亲教我怎么做梦。她说给我弟弟听的,那时他分不清梦和现实。我分清了,但我看不住梦里的东西,也不能安排我的梦。
在梦中你由不得自己。母亲说。梦中你变成啥就安心当啥,不要去想。别人追你就跑。跑着跑着会飞起来。跑不掉就跑不掉。死了也不要紧。不要扭着梦。在梦中我们看见自己在做什么,甚至看见自己的脊背,说明我们的眼睛在别处。而在现实中我们看见的都是别人。那时眼睛在自己头上。知道这一点,你就能准确判断自己在梦中,还是醒了。梦是给瞌睡安排的另一种*活。在那里,我们奔跑,不用腿。腿一动不动,看见了自己的奔跑。跑着跑着飞起来。飞起来就好了。一场梦里,只有一个人会飞。因为每一场梦,只配了一对翅膀,或者一个飞的愿望。你飞起来了,其他人就全留在地上。
或许家里没有一个人,炕空空的。人去忙活梦中的事情。一些人回到早年,发现许多人都没长大,小小的,自己也是几十年前的样子。长大的那些人又是谁。几乎所有的活没有干完。我们自以为收回来吃掉的那些粮食,全长在地里。
刘二爷说,我们最后有可能被自己的梦吃掉。因为我们醒来后,做过的梦还在继续。
梦是我们**不息的子孙。在我们无限繁殖的梦里,我们永远是孩童。
所有路都走遍了。每人都想把村子带到自己的路上。夜晚他们暗暗围在一起,讲自己找到的路,尤其跑顺风买卖的,跑遍这片荒野,知道的路比我们的头发还多。可是,他们都对别人不屑一顾。当冯七说出一条通向柳户地的路时,韩三就会反驳,我跑遍了荒野,怎么从来没看见没听说这样一条路。而韩三说出走荒舍的一条路时,王五又提出同样的置疑。
谁都看不见别人走过的路。围在油灯下的一村庄人,谁看谁都是黑的。一个村庄,不可能走上一条只有一个人知道的路。
可是我不认识白天。我看见的白天全是别人的。我在太阳底下出过汗,追过自己的影子。以后全是黑夜,他们做梦的时候我醒来。我用他们的镰刀割麦子,穿他们脱在炕头的鞋,在村里村外的路上,来回的走,留下他们的脚印。
起先夜里有守夜人,有不愿离开的夜行者。我看见黑暗中的粮食,看见星光下的播种,和收割。看见尘土,在黑夜中的飘起沉落,看见镰刀暗暗的磨损。后来守夜人走了,他们都不在了,整个夜晚剩下我一个人。我试图从一个又一个黑夜走到白天。走着走着我睡着了。醒来依旧是黑夜。我看见的全是他们的梦,像一座一座的坟墓,孤悬在夜空。每个人都埋在自己的梦里。
而在整个白天,村庄上空孤零零的,悬着我一个人的梦。
仿佛我一直站在童年的旷野,看着自己渐渐长大的身影走远,混入远处的人群,再认不出来。那时他们像树一样草一样在天边摇曳,像黑夜的风一样,我是他们中的一个。他们又是谁。我只是在五岁的早晨,看见他们赶车出村,看见混在他们中间的我自己,坐在一辆马车上,脸朝后,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子。我没扭头朝前看,不知道赶车的人是谁。也许没有赶车人,只是马自己在走,车被一场风吹着在动。以后的事我再记不清,不知道我去了哪里。也许哪都没去,那个早晨走远的全是别人。我在他们中间,看见一个是我的人,我一直看着他走远。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在远处他们每人走一条路,那些路从不交叉,他们从不相遇。每个人的经历都无人证实。像飘过天空的叶子,没有被另外的叶子看见。见证他们的是一场一场的风。那些风真的刮过荒野吗。一场一场的风在村里停住。或许根本没有风。在虚土庄某一天的睡梦中,一百年的岁月开花了。我闻到远处的芬芳。看见自己的人群,一千一万个我在荒野上走动。我在虚土梁上的小村庄里,静静的看见他们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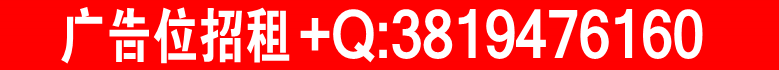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